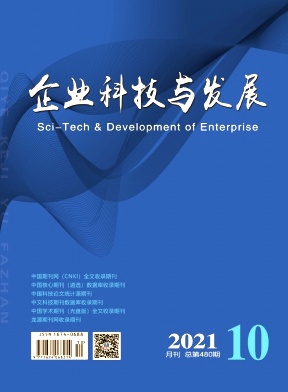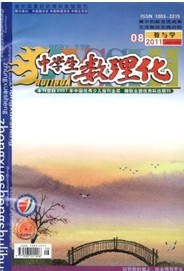庄子的不哭与哭
在我的想象和印象中,庄子的学问和生活处处充满着悖论,这一点同样也演绎到庄子的不哭与哭的二元对立上。庄子确实不爱哭甚至不会哭,连他相以为命的妻子死的时候,他不仅不哭,而且还鼓盆而歌。但庄子确实哭过。那是当他看到他的最好的朋友,几乎也是唯一的朋友,名辩家惠施的坟墓之后,他便席地而哭,泣不成声了。
大凡喜怒哀乐、哭骂笑谈,乃人之常情。生活中谁个不会哭?谁个没哭过?20年前,第一次从鸡犬之声相闻的偏僻山村走向喧嚣嘈杂的大都市的我,是一个稚气未脱、时不时都要流泪的毛孩子。记得刚到大学报到时,我因为丢失了入学通知书曾当众而泣,又因为持久的胃肠道不适曾黯自落泪。要知道,那是一个十几岁的毛孩子被孤身一人地搁置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又遭此不幸,焉有不哭之理?可当我在一天晚上,手捧一本叫做《中国古代哲学寓言故事选》的书在饶有兴趣地阅读时,我突然发现世界上竟有不会哭、不爱哭、不能哭之人,这个人就是后来我才知道其名气大得令人吃惊的大文人庄周。那是一本被秀丽的兰色覆裹着的厚厚的通俗读物,它的编著者是我所敬仰的复旦大学的严北溟先生。我在其中看道:庄子妻子死了,他的好朋友惠施去看望他。当惠施心情沉重的地走入他家时,被眼前的景象弄懵了:庄子不仅不哭,还坐到妻子的棺材上敲击着瓦盆放声高唱。依我当时的心情,总觉得这位庄先生太绝情了。尽管我看到了他对惠施那段有关生死(有无)转化的高深莫测地解释,也明白了人生在世,不过是无中生有;人死了,不过是有还于无,用俗话说是又打回老家去了。庄子歌而不哭,自有他的形而上的理由,因为他在精神上欢送妻子胜利凯旋。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懵懂少年,我还是觉得庄子这个人太过神经兮兮了。但因此,也使我结识了这位无法直面其人的大文人,或许他的鼓盆而歌便是他的个性,它豫示着这位大文人不同凡响的心路历程。所以,当我想到这一层时,我便又转变了自己的立场,开始对之产生了浓厚兴趣,以之于连我的毕业论文直至今日的部分学术研究均与庄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15年前,当我在北大听陈鼓应先生讲老庄哲学时,曾打算就庄子的“不哭论”的更深层的生存意味求教于陈先生,但那不过是一闪之念,转眼便放弃了打算。因为我害怕先生做大学问而不理会此等怪问,虽然陈先生一直如庄周一般风趣。就在那年深秋,我去拜访宗白华先生时,内心中又有了提及此事的冲动。但当我坐入宗先生的书房后,便再也没有机会向他提及此事。宗先生当时已八十有五,且精神钁铄地跟我等无名晚辈大谈中西园林空间意识的异同,我实在不想打断先生兴味正浓的美学散步。等宗先生的美学散步停顿下来时,因害怕先生劳累,便起身告辞了。所以,此事再度被搁置了起来。我一向认为,在当代汉学界,最能洞悉庄周心迹的,不过陈先生和宗先生二人。所以,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就此事向别人追问的打算。渐渐地也就觉得这件事不那么重要了。 然而,庄子并非永远不哭之人,他远非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当我有暇去字斟句酌地阅读《庄子》全书时,我发现他也有过老泪纵横地经历,他哭过。其时,我略感惊讶,这位幽默得令人难以招架的讽刺高手,怎么说哭就哭了呢?是啊,人非草木,焉能无情?虽然他教给人们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道理,但他自己并没有做到。他的那次哭,是由于友谊的失落和精神对话者的遽然驾鹤西游带来的,因为他看到了他的好友惠施的坟墓。因为惠施的撒手西去,再也不会有人问他儵鱼为什么是快乐的、葫芦和大树是否真的无用,总之,再也不会有人与他谍谍不休地争论了。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起来,这一回庄子真的伤心了(尽管这与他的学问不符),因为他失去了友谊层面上唯一的精神寄托。也难怪,世事沧桑,真情难觅。人生在世得一知己者足矣!作为与世俗格格不入的出世文人,庄子何尝不是如此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庄周其人其说更进一步的了解,我对庄周的不哭与哭有了更加理性化地认识。就人生哲学的层面上讲,我发现他的不哭与他的人生观有着密切联系。他痛斥虚情假意,所以他大骂世儒俗士;他厌恶装腔作势,所以他讽刺东施效颦;他反对人们情绪化地处理一切事务,所以他为比干刨心而惋惜。他甚至教人们如何如何地坐忘怀道;如何如何地练就“喜怒哀乐不入乎胸次”的功夫。因为他要人们逃离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的陷阱,逃离斤斤计较、小题大做、多愁善感的世俗情怀,他要人们学会精神上的彻底地自由和解脱。他是一位绝对意义上的文人。同时也发现,他的哭是对人生真情的不自觉地依恋,是从超越还原到随俗,是对不哭的反动同时也是对不哭的补充。因为他毕竟也是人,是有血有肉、崇尚真情、注重纯真友谊的清逸之士。只不过他的追求过于心灵化、内在化、艺术化了。
现如今,市场经济汹涌澎湃,人情世故尘滓泛起。有的人为利益可以出卖灵魂,有的人为利益可以出卖肉体,有的人为利益可以出卖爱情,有的人为利益可以出卖友谊。在这种情况下,再去谈什么庄子的不哭与哭,似乎已毫无意义,而且不合时宜。因为庄子的故事根本不适合现代和后现代,它太古董了。但令我迷惑不解的是,作为还守持着某种清高本分的普通知识分子,我们不去谈论类似的这些故事,又能谈论些什么呢?我真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