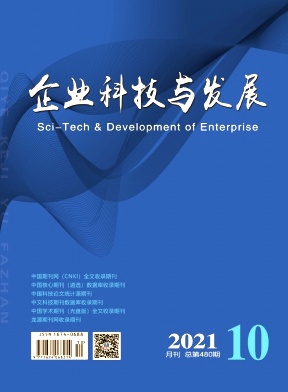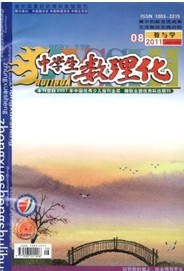浅析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抗日小说
论文摘要: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抗日小说以本民族精神及本民族体验的真实性而与其他的抗日小说有明显不同的风格,特别是把原住民的原始英雄主义与抗日精神结合来写的作品,一方面显示了原始英雄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意义体现,另一方面这样的作品既显示了原住民作家创作的独特性,也显示了这样的题材也许只能是原住民作家才可拥有的专利和特长。
台湾新文学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至1945年日本投降时经历了二十多年不平常的文学发展。不平常之处在于,爱国进步作家在艰难环境下坚持文学创作,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大部分作品以“压不扁的玫瑰”的精神傲立日本统治下的文坛,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倡导抵制日本文化,表现了台湾人民的斗争意志。“抗日主题”是台湾新文学的闪光主题,它使台湾新文学主流如淬火的钢一般强度倍增。
日据时期,台湾原住民各族群同样受到日本人的侵略和压迫,台湾原住民各族群人民也同样积极奋起反抗,从军事上打击日人,从文化上抵制日人,英勇顽强,令日人害怕。遗憾的是,台湾新文学表现原住民抗日英雄事迹的作品,时隔六十多年后才出现。主要作品有泰雅族作家游霸士·挠给赫的系列短篇小说《丸田炮台进出》、《兄弟出猎》、《出草》、《大霸风云》、《断层山》;布农族作家霍斯陆曼·伐伐的短篇小说《失手的战士》。还有其他作家的散文、小说有一些零星片段的涉及。目前,虽然原住民作家抗日小说还不是很多,但却在文学的天空里亮起了火花,具有特殊的意义:原住民作家的“抗日主题”继承并发展了台湾新文学的战斗精神和文学传统,弘扬了原住民人民的爱国精神;原住民作家以文学创作首次揭露了日本侵略军在原住民地区的罪行,首次真实地描写了原住民的抗日斗争生活;在表现原住民抗日斗争情况时,原住民作家的“原味表现”不同于台湾的新文学作家们,也不同于大陆的抗日小说,情节、语言、人物形象等均有突出的原住民族风格。在台湾乃至中国文坛上,原住民作家的抗日小说以自己独特的贡献展现了独特的魅力。
1985年1月5日,台湾《自立晚报》刊登了一篇散文,作者是泰雅族作家瓦历斯·诺干,记述的是:作者到山东威海参加一个“人与大自然”的会议,其间来到当年日军登陆中国的刘公岛,作者想起了1895年4月14日清政府与日本签定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岛屿及其附属岛屿。这时,旁边有人说“这是中国的痛”,作者的心更为痛楚,因为中国水师的惨败,“改变而且决定了台湾1895年以后的原住民悲惨的历史命运”。从这一天起,原住民和台湾被沦为日本人的奴隶;从这一天起,原住民的家园被销毁,土地被管制,自由被锁定,那一圈圈带电的铁丝网象魔鬼般缠绕在美丽的绿林山坡上;但也是从这一天起,爱好和平的原住民拿起了射击野兽的土制猎枪,挥着砍山开路的大刀,向日本人宣战。
对于这段历史,史学家们这样写:
1896年,高雄阿斯本社、台中丘则卡斯社的原住民人民顽强抗击日军的“讨伐”;
1897年,花莲太鲁阁高山族人民在抗击日军“讨伐”的战役中,据险反击,重创日军,日军除出动花莲全部守备外,又从基隆调台北调兵增援,原住民人民顽强拼杀,使日军伤亡惨重,迫使日军只得收兵;
1898年,下淡水溪原住民700余人杀死日本濑户署长:
1900年,1901年,1902年……
1930年,台中州雾社地方的原住民(泰雅族)不堪日本人的肆意杀戮、掠夺和压迫,举行雾社起义,打死打伤侵略者四千多人,虽然起义被日本侵略者镇压了.但它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原住民族的抗日情绪,当时大陆民众也给予热情的声援,北京出版的《新东方杂志》发表评论声讨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连日本民众和日本国内舆论都一致加以谴责……
对于这段历史,文学家没有像史学家那样用数字说话,而是把数字变成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变成富于人物性格并属于那个民族性格的语言,变成动感突出的各种行动,形象地描写出日据下的原住民抗日精神的顽强不屈。泰雅族作家游霸士·挠给赫的《丸田炮台进出》一开头写到:“这些脸上毫无表情,没必要时,整天说不上两句话,总显得有些土里土气的部落勇士,竞使用三四条人家造得很坏的火枪、几把弓箭和番刀去敌对日军架在二本松山顶丸田炮台上的3门可怕的太母山炮和几铤水冷式重型机枪以及无数人手一把三八式步枪的英勇日军野战师团精兵。”l2J作家用一种简短的句子把泰雅勇士的精神表达给读者感受,这样的表达是简单传神有力并富于个人风格和民族特点的,尤其是非常准确的抓住了泰雅勇士的风格风度及其在抗日行动中富于民族特点的精神状态。《丸田炮台进出》写一个以少战多、以弱斗强的故事,正面描写了原住民英勇作战的抗日精神。尽管泰雅族与日本侵略者在物质上、武器上完全不可比,日本人有步枪、重型机枪、大炮、带电的铁丝网、日本军刀,泰雅族只有番刀、自制铅弹、弓箭,铅弹的铅还是用故意引诱日本人打炮得到的炮弹壳做的。但是,日本人嚣张又心怀巨大的恐惧,泰雅勇士沉着又坚信顽强的决心。所以,“我”所在的大狗部落只选了6个勇士就敢去偷袭二本松山顶上的敌炮大队。当太阳散发晨光时,“6个人都站起来,把头伸出箭竹林上面开枪了。尤饶·亚悠特的箭一根接一根咻咻地飞出去。原来集合着的日本兵,一个个吓呆了……”个人毫不惧怕人少武器旧,他们土法上马却万分认真地进行着他们的抗日行动,他们坚信:无论如何,抗日,一定要打,顽强地打,狠狠地打。
作为反映原住民日据生活的文学作品,原住民作家特点是抓住民族的内在心理、情感和习俗等属于原住民特质的方方面面去表现本民族的抗日精神,同时又努力再现战争映衬下原住民的生活与习俗,处处真实地描写原住民抗日的顽强精神,又处处写到原住民抗日精神与原住民原始习俗碰撞后出现的些微变形状态。比如6个人偷袭敌炮阵地,这是何等顽强的对敌精神!但是说是去与日本人打仗,却像是去打猎,好比打山猪、打狐狸、打狼,出征前一切按打猎习俗行事,如不碰女人的东西,要占卜(水占、竹占、鸟占)、测梦等,大吉大利一定出征,不吉不利就不出征;梦吉的人按计划出征,梦凶的人再勇猛也不能出征;即使是走在半道上了,一旦发现有不吉之兆立即收兵,班师回寨。《丸田炮台进出》中那位泰雅勇士飞苏·瓦旦出征前一晚做了个恶梦,第二天就被禁止出征,尽管他在头目面前流泪请求破例,但最终未被允许。本来多一个人多一分力量,何况偷袭炮台也不过6个人,但头目老爹一定不让他去,因为不能违背神的明示。于是,原住民主观上的抗日狂飙精神因风俗而被限制。这也说明,当时原住民普遍对日本人侵吞台湾的野心认识不足,他们中不少人把日本的侵略行径仅看成是又来了一种争夺土地的“动物”——日本人只是有武器的“野兽”,而轻视了侵略者的残酷和野心。有趣的是,这样的“轻敌”思想反倒在无形中增加了原住民族打击侵略者的信心,因为对打猎有着丰富经验的民族而言,“野兽”没什么可怕的。
了解了原住民作家开阔的胸襟和尊重真实生活的思想,就能理解原住民作家在抗日小说中张扬民族原始英雄主义,即“出草”风俗(俗称猎人头)的勇气和意义了。为什么写“出草”需要勇气?这是由历史因素和现代背景决定的。在历史上,“出草”的习俗不仅只是台湾原住民才有的古老习俗,云南的佤族及世界上其他一些古老的民族也有这一习俗。“出草”的意义对拥有这一习俗的民族而言是极重要的,但是“出草”的含意各个民族可能不是完全一致。台湾原住民中曾有过这一习俗的民族有泰雅族、布农族、曹族、排湾族。“出草”的基本含义大体是:男性成年的标志,战争时必须砍走敌首的要求,训练胆识的途径,证明清白的方法。总之,这应该是衡量男性英雄的一个重要标准,它体现了这些民族原始而古老的英雄主义观念。这个习俗在没有外来观念进入前一直保存着原生态的发展,原住民也习以为常。但是,当台湾社会的发展有了新的人群、新的观念、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文化取舍后,这个习俗就受到很大的冲击。由于与生命相关,因而这个习俗存在的合理性就受到质疑。现代社会不能接受英雄主义以那样一种方式表现出来,现代社会还造了一个词——“野蛮”来形容它。而这一发展过程中也有传说:汉族曾有一个叫“吴凤”的商人,据汉人说他出于真心帮助原住民经商,因感于“出草”对生命的危害,自愿献身,他告诉原住民,有一天有一个身披红袍的人会骑马经过,后来果真有一个这样的人经过,按照“出草”风俗,原住民猎下了此人人头,却发现是他们最爱的吴凤,从此这个部族不再猎头了。
泰雅族作家游霸士·挠给赫和布农族作家霍斯陆曼·伐伐以极大的勇气描写了“出草”风俗,而且没有把“出草”仅作一般意义的、风俗介绍般的描写,而是把勇士“出草”的事件选择在日据时期,写“出草”在对日斗争中所焕发出的抗击外族侵略的新含义、新意义。
游霸士·挠给赫直接给小说取名《出草》,小说用第一人称、个人叙述视角,从死了几十年的巴彦·哈用在冥界的回忆开始,倒叙他为什么躺在一个阴冷的山崖下。作者选择了一个独特的、与内容极相适应的叙述方式结构小说,使这篇小说从一开始就置于一个真实、坦诚的氛围之中,使读者体会得到作家同样坦诚的创作态度:当年“我”是一个泰雅青年,却因在捕鱼时把渔具错放到相邻马都安部落的水域被马都安部落的人以为“我”偷盗而一路追杀。尽管“我”是误放,但按两个部落具有法律效力的民间规矩办,“我”要通过“出草”证明自己的清白,砍一个人头回来。“我”杀死了取水的日本老兵的头颅,向族人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日本人把“我”抓去判死罪,在执行枪决时,“我”和杀“我”的日本兵一起坠入山崖,死了。所以,几十年来我都躺在阴冷的山崖下,与“我”相伴的除了故乡的林木,竞就是“我”的敌人——日本兵—葬身异国他乡的侵略者士兵。由于山洪冲下一块巨石挡住了“我”和日本兵向人眺望、与人间交流的机会,3个无所依靠的曾经为敌的鬼魂只得“今日为友”常常聊天了。日本兵很奇怪“我”为什么要杀死他们的那个文职老兵,说这老兵其实已不是兵了,他已退伍,正等着有船回日本与妻儿团聚。“我”告诉他们,“我”之所以这样,“一来可以洗刷我的罪名”,二来也可警告马都安部落的人“我们的居民是不容欺负的”,最后也是最神圣的是“我们的祖先遗留下来的领土更不容侵犯”。作者运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以及“我”与两个日本兵的对话把不同的内心情绪和心理状态直接传达出来。“我”虽死却倍觉英勇和光荣,因为这一死,不仅证实了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勇士,更光荣的是实现了一个勇士为国捐躯的最高理想,那是一种多么热血沸腾的情怀啊!
当猎取到人头时,巴彦·哈用充满自豪,“四周望去,好一片河山。此刻,红彤彤的太阳还在阿娃泥山顶上面不远的天空上高高悬着,射下万道霞光。在黄昏的余光中,照得原始森林象火烧着了一般,也把山下的泰雅部落染成血红色”。猎首的原始英雄主义在此展现了最光芒的新意义和新精神。巴彦·哈用的遭遇把“出草”在族群记忆中的习俗意义通过个人的经历叙述出来,使世人明白和理解了“出草”这个特殊习俗过去存在的历史条件和它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转变。而通过巴彦·哈用的视点,读者还看见了霸道横行的侵略者的另一面:两个日本兵思念故国愁闷不已,还有那个老兵,作为侵略者,他们是罪恶的魔鬼,但作为家庭的一员,他们是多么不幸。这两个日本兵天天向故乡鞠躬,天天唱一首挽歌“花虽芳香终必散落,婆裟世界孰能常存,今日越过有为之奥山,浅梦不见又不醉。唱完嘤嘤啜泣”。作者深刻地揭示侵略战争在给他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给本民族、尤其是充当炮灰的个人带来极大的苦难。
布农族作家霍斯陆曼·伐伐的小说《失手的战士》,分为“被大火诅咒的小女孩”、“忿怒·耻辱·敌人”、“爸爸不吉利的梦”、“作战·出草”、“失手”、“蒲公英般的族群”六节内容,顺叙写出督布斯“出草”的缘由、过程到失手终致失败的结果。这篇小说以“出草”的结局写得最为精彩。
督布斯小时侯因玩火引发人火,烧伤了幼小的妹妹,族人迷信这是督布斯家触犯神灵招致的惩罚,族中长老怕神灵再降罪于部落,要督布斯的父母掐死女儿,但督布斯的父母不忍那样做。督布斯的爸爸从此被禁止与部落人一起去打猎。日本人人侵后,要求部落把猎枪全部交出去,另外还制定了很多侮辱限制族人的规定。部落忍无可忍,决定主动打击日本人。督布斯的爸爸此时做了一个不吉利的梦,失去出征的机会。经过争取,族里决定让督布斯代父出征,砍杀敌人的头颅回来洗刷家庭的罪。督布斯出战了,他这一次必须砍敌首回部落立功赎罪,为他的家庭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但是,正当督布斯跳进敌人的窝点时,发现没有其他的敌人,只有一个日本女人,督布斯带着杀红了眼的杀气砍下一刀,却把刀砍进了女人旁边的一棵木柱里。在督布斯拔刀之时,女人宽大的日本衣服下露
出一个小女孩的脸,女孩眼含泪水并颤栗着,督布斯一下子想起自己的妹妹烧伤的痛楚。这时有人喊:“督布斯,你快砍了头走,敌人的援兵会很快到的。”督布斯挥刀砍倒木头房子的支架,并把房子推向山沟,然后挥刀割下日本女人的一绺头发,追赶队伍去了。回部落后,有人说听到督布斯进的木屋有女人声音,怎么就没砍下人头呢?督布斯说那人跳崖了,他只捡到头发,他拿出自己故意割的头发违心地为自己作证。后来妹妹问他缘由时,督布斯告诉妹妹:“因为我不想杀自己的妹妹。”他讲了一个其他的故事给妹妹听,不想让妹妹再问他砍日本人人头的事,聪明的妹妹了解了一切,打断他的话问:“她能不能算是我的妹妹?”督布斯回答:“不能,因为她们的神和我们的神不是住在同一个地方。”再后来,日本人杀害了布农族的抗日首领,占领了布农族地区。日本人常常集中部落族人,强行发日用品给族人。一次,督布斯也被押去领日本人的东西,有一个妇女拿着一捆棉被向他走来,弯腰并说了一长串日语,旁边懂日语的部落老人告诉他:“她的女儿已经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去读书,不久的将来她也要回去照顾她的女儿,这个棉被表示她的谢意。督布斯,你认识她?”原来这位给他棉被的日本妇女就是他欲杀而又放走的日本女人。
这是一个忧伤的故事,主人公督布斯的行动没有挽救自己家庭的荣誉,反救了敌人中间的无辜者——日本母女。督布斯个人也由此陷入一个悲剧,他无法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线,但他又无法不为自己辱没了祖先习俗的举动而感到羞愧和愤懑。这让一个极想成为英雄的布农男孩不得不负担一生的心理耻辱:个人为家庭奋斗的理想没有实现,集体的使命又象蒲公英般飘零飞荡,对一个男孩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但是,恰恰是这个沉重打击显示的悲剧意义揭示了布农族传统人文观念里关于善、恶的近乎真理性的认识:“生命是由善、恶组成的,但生命具有选择善、恶的权力”。男孩督布斯凭借自我经验和智慧选择了“善”的举动,彰显了原始习俗中强调正义及善良精神的本质存在。
如今,日本侵略者早已被打败,抗日战争胜利已60周年,但是原住民抗日文学的解读才开始。和平年代里,反映战争的文学创作和解读、反映战争的文学作品是对战争和侵略者是一种警示,一种警惕,对爱好和平的人们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再认同。
投稿方式:
电话:029-85236482 15389037508 13759906902
咨询QQ:1281376279
网址: http://www.xinqilunwen.com/
电子投稿:xinqilunwen@163.com 注明“所投期刊”
台湾新文学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至1945年日本投降时经历了二十多年不平常的文学发展。不平常之处在于,爱国进步作家在艰难环境下坚持文学创作,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大部分作品以“压不扁的玫瑰”的精神傲立日本统治下的文坛,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倡导抵制日本文化,表现了台湾人民的斗争意志。“抗日主题”是台湾新文学的闪光主题,它使台湾新文学主流如淬火的钢一般强度倍增。
日据时期,台湾原住民各族群同样受到日本人的侵略和压迫,台湾原住民各族群人民也同样积极奋起反抗,从军事上打击日人,从文化上抵制日人,英勇顽强,令日人害怕。遗憾的是,台湾新文学表现原住民抗日英雄事迹的作品,时隔六十多年后才出现。主要作品有泰雅族作家游霸士·挠给赫的系列短篇小说《丸田炮台进出》、《兄弟出猎》、《出草》、《大霸风云》、《断层山》;布农族作家霍斯陆曼·伐伐的短篇小说《失手的战士》。还有其他作家的散文、小说有一些零星片段的涉及。目前,虽然原住民作家抗日小说还不是很多,但却在文学的天空里亮起了火花,具有特殊的意义:原住民作家的“抗日主题”继承并发展了台湾新文学的战斗精神和文学传统,弘扬了原住民人民的爱国精神;原住民作家以文学创作首次揭露了日本侵略军在原住民地区的罪行,首次真实地描写了原住民的抗日斗争生活;在表现原住民抗日斗争情况时,原住民作家的“原味表现”不同于台湾的新文学作家们,也不同于大陆的抗日小说,情节、语言、人物形象等均有突出的原住民族风格。在台湾乃至中国文坛上,原住民作家的抗日小说以自己独特的贡献展现了独特的魅力。
1985年1月5日,台湾《自立晚报》刊登了一篇散文,作者是泰雅族作家瓦历斯·诺干,记述的是:作者到山东威海参加一个“人与大自然”的会议,其间来到当年日军登陆中国的刘公岛,作者想起了1895年4月14日清政府与日本签定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岛屿及其附属岛屿。这时,旁边有人说“这是中国的痛”,作者的心更为痛楚,因为中国水师的惨败,“改变而且决定了台湾1895年以后的原住民悲惨的历史命运”。从这一天起,原住民和台湾被沦为日本人的奴隶;从这一天起,原住民的家园被销毁,土地被管制,自由被锁定,那一圈圈带电的铁丝网象魔鬼般缠绕在美丽的绿林山坡上;但也是从这一天起,爱好和平的原住民拿起了射击野兽的土制猎枪,挥着砍山开路的大刀,向日本人宣战。
对于这段历史,史学家们这样写:
1896年,高雄阿斯本社、台中丘则卡斯社的原住民人民顽强抗击日军的“讨伐”;
1897年,花莲太鲁阁高山族人民在抗击日军“讨伐”的战役中,据险反击,重创日军,日军除出动花莲全部守备外,又从基隆调台北调兵增援,原住民人民顽强拼杀,使日军伤亡惨重,迫使日军只得收兵;
1898年,下淡水溪原住民700余人杀死日本濑户署长:
1900年,1901年,1902年……
1930年,台中州雾社地方的原住民(泰雅族)不堪日本人的肆意杀戮、掠夺和压迫,举行雾社起义,打死打伤侵略者四千多人,虽然起义被日本侵略者镇压了.但它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原住民族的抗日情绪,当时大陆民众也给予热情的声援,北京出版的《新东方杂志》发表评论声讨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连日本民众和日本国内舆论都一致加以谴责……
对于这段历史,文学家没有像史学家那样用数字说话,而是把数字变成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变成富于人物性格并属于那个民族性格的语言,变成动感突出的各种行动,形象地描写出日据下的原住民抗日精神的顽强不屈。泰雅族作家游霸士·挠给赫的《丸田炮台进出》一开头写到:“这些脸上毫无表情,没必要时,整天说不上两句话,总显得有些土里土气的部落勇士,竞使用三四条人家造得很坏的火枪、几把弓箭和番刀去敌对日军架在二本松山顶丸田炮台上的3门可怕的太母山炮和几铤水冷式重型机枪以及无数人手一把三八式步枪的英勇日军野战师团精兵。”l2J作家用一种简短的句子把泰雅勇士的精神表达给读者感受,这样的表达是简单传神有力并富于个人风格和民族特点的,尤其是非常准确的抓住了泰雅勇士的风格风度及其在抗日行动中富于民族特点的精神状态。《丸田炮台进出》写一个以少战多、以弱斗强的故事,正面描写了原住民英勇作战的抗日精神。尽管泰雅族与日本侵略者在物质上、武器上完全不可比,日本人有步枪、重型机枪、大炮、带电的铁丝网、日本军刀,泰雅族只有番刀、自制铅弹、弓箭,铅弹的铅还是用故意引诱日本人打炮得到的炮弹壳做的。但是,日本人嚣张又心怀巨大的恐惧,泰雅勇士沉着又坚信顽强的决心。所以,“我”所在的大狗部落只选了6个勇士就敢去偷袭二本松山顶上的敌炮大队。当太阳散发晨光时,“6个人都站起来,把头伸出箭竹林上面开枪了。尤饶·亚悠特的箭一根接一根咻咻地飞出去。原来集合着的日本兵,一个个吓呆了……”个人毫不惧怕人少武器旧,他们土法上马却万分认真地进行着他们的抗日行动,他们坚信:无论如何,抗日,一定要打,顽强地打,狠狠地打。
作为反映原住民日据生活的文学作品,原住民作家特点是抓住民族的内在心理、情感和习俗等属于原住民特质的方方面面去表现本民族的抗日精神,同时又努力再现战争映衬下原住民的生活与习俗,处处真实地描写原住民抗日的顽强精神,又处处写到原住民抗日精神与原住民原始习俗碰撞后出现的些微变形状态。比如6个人偷袭敌炮阵地,这是何等顽强的对敌精神!但是说是去与日本人打仗,却像是去打猎,好比打山猪、打狐狸、打狼,出征前一切按打猎习俗行事,如不碰女人的东西,要占卜(水占、竹占、鸟占)、测梦等,大吉大利一定出征,不吉不利就不出征;梦吉的人按计划出征,梦凶的人再勇猛也不能出征;即使是走在半道上了,一旦发现有不吉之兆立即收兵,班师回寨。《丸田炮台进出》中那位泰雅勇士飞苏·瓦旦出征前一晚做了个恶梦,第二天就被禁止出征,尽管他在头目面前流泪请求破例,但最终未被允许。本来多一个人多一分力量,何况偷袭炮台也不过6个人,但头目老爹一定不让他去,因为不能违背神的明示。于是,原住民主观上的抗日狂飙精神因风俗而被限制。这也说明,当时原住民普遍对日本人侵吞台湾的野心认识不足,他们中不少人把日本的侵略行径仅看成是又来了一种争夺土地的“动物”——日本人只是有武器的“野兽”,而轻视了侵略者的残酷和野心。有趣的是,这样的“轻敌”思想反倒在无形中增加了原住民族打击侵略者的信心,因为对打猎有着丰富经验的民族而言,“野兽”没什么可怕的。
了解了原住民作家开阔的胸襟和尊重真实生活的思想,就能理解原住民作家在抗日小说中张扬民族原始英雄主义,即“出草”风俗(俗称猎人头)的勇气和意义了。为什么写“出草”需要勇气?这是由历史因素和现代背景决定的。在历史上,“出草”的习俗不仅只是台湾原住民才有的古老习俗,云南的佤族及世界上其他一些古老的民族也有这一习俗。“出草”的意义对拥有这一习俗的民族而言是极重要的,但是“出草”的含意各个民族可能不是完全一致。台湾原住民中曾有过这一习俗的民族有泰雅族、布农族、曹族、排湾族。“出草”的基本含义大体是:男性成年的标志,战争时必须砍走敌首的要求,训练胆识的途径,证明清白的方法。总之,这应该是衡量男性英雄的一个重要标准,它体现了这些民族原始而古老的英雄主义观念。这个习俗在没有外来观念进入前一直保存着原生态的发展,原住民也习以为常。但是,当台湾社会的发展有了新的人群、新的观念、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文化取舍后,这个习俗就受到很大的冲击。由于与生命相关,因而这个习俗存在的合理性就受到质疑。现代社会不能接受英雄主义以那样一种方式表现出来,现代社会还造了一个词——“野蛮”来形容它。而这一发展过程中也有传说:汉族曾有一个叫“吴凤”的商人,据汉人说他出于真心帮助原住民经商,因感于“出草”对生命的危害,自愿献身,他告诉原住民,有一天有一个身披红袍的人会骑马经过,后来果真有一个这样的人经过,按照“出草”风俗,原住民猎下了此人人头,却发现是他们最爱的吴凤,从此这个部族不再猎头了。
泰雅族作家游霸士·挠给赫和布农族作家霍斯陆曼·伐伐以极大的勇气描写了“出草”风俗,而且没有把“出草”仅作一般意义的、风俗介绍般的描写,而是把勇士“出草”的事件选择在日据时期,写“出草”在对日斗争中所焕发出的抗击外族侵略的新含义、新意义。
游霸士·挠给赫直接给小说取名《出草》,小说用第一人称、个人叙述视角,从死了几十年的巴彦·哈用在冥界的回忆开始,倒叙他为什么躺在一个阴冷的山崖下。作者选择了一个独特的、与内容极相适应的叙述方式结构小说,使这篇小说从一开始就置于一个真实、坦诚的氛围之中,使读者体会得到作家同样坦诚的创作态度:当年“我”是一个泰雅青年,却因在捕鱼时把渔具错放到相邻马都安部落的水域被马都安部落的人以为“我”偷盗而一路追杀。尽管“我”是误放,但按两个部落具有法律效力的民间规矩办,“我”要通过“出草”证明自己的清白,砍一个人头回来。“我”杀死了取水的日本老兵的头颅,向族人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日本人把“我”抓去判死罪,在执行枪决时,“我”和杀“我”的日本兵一起坠入山崖,死了。所以,几十年来我都躺在阴冷的山崖下,与“我”相伴的除了故乡的林木,竞就是“我”的敌人——日本兵—葬身异国他乡的侵略者士兵。由于山洪冲下一块巨石挡住了“我”和日本兵向人眺望、与人间交流的机会,3个无所依靠的曾经为敌的鬼魂只得“今日为友”常常聊天了。日本兵很奇怪“我”为什么要杀死他们的那个文职老兵,说这老兵其实已不是兵了,他已退伍,正等着有船回日本与妻儿团聚。“我”告诉他们,“我”之所以这样,“一来可以洗刷我的罪名”,二来也可警告马都安部落的人“我们的居民是不容欺负的”,最后也是最神圣的是“我们的祖先遗留下来的领土更不容侵犯”。作者运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以及“我”与两个日本兵的对话把不同的内心情绪和心理状态直接传达出来。“我”虽死却倍觉英勇和光荣,因为这一死,不仅证实了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勇士,更光荣的是实现了一个勇士为国捐躯的最高理想,那是一种多么热血沸腾的情怀啊!
当猎取到人头时,巴彦·哈用充满自豪,“四周望去,好一片河山。此刻,红彤彤的太阳还在阿娃泥山顶上面不远的天空上高高悬着,射下万道霞光。在黄昏的余光中,照得原始森林象火烧着了一般,也把山下的泰雅部落染成血红色”。猎首的原始英雄主义在此展现了最光芒的新意义和新精神。巴彦·哈用的遭遇把“出草”在族群记忆中的习俗意义通过个人的经历叙述出来,使世人明白和理解了“出草”这个特殊习俗过去存在的历史条件和它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转变。而通过巴彦·哈用的视点,读者还看见了霸道横行的侵略者的另一面:两个日本兵思念故国愁闷不已,还有那个老兵,作为侵略者,他们是罪恶的魔鬼,但作为家庭的一员,他们是多么不幸。这两个日本兵天天向故乡鞠躬,天天唱一首挽歌“花虽芳香终必散落,婆裟世界孰能常存,今日越过有为之奥山,浅梦不见又不醉。唱完嘤嘤啜泣”。作者深刻地揭示侵略战争在给他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给本民族、尤其是充当炮灰的个人带来极大的苦难。
布农族作家霍斯陆曼·伐伐的小说《失手的战士》,分为“被大火诅咒的小女孩”、“忿怒·耻辱·敌人”、“爸爸不吉利的梦”、“作战·出草”、“失手”、“蒲公英般的族群”六节内容,顺叙写出督布斯“出草”的缘由、过程到失手终致失败的结果。这篇小说以“出草”的结局写得最为精彩。
督布斯小时侯因玩火引发人火,烧伤了幼小的妹妹,族人迷信这是督布斯家触犯神灵招致的惩罚,族中长老怕神灵再降罪于部落,要督布斯的父母掐死女儿,但督布斯的父母不忍那样做。督布斯的爸爸从此被禁止与部落人一起去打猎。日本人人侵后,要求部落把猎枪全部交出去,另外还制定了很多侮辱限制族人的规定。部落忍无可忍,决定主动打击日本人。督布斯的爸爸此时做了一个不吉利的梦,失去出征的机会。经过争取,族里决定让督布斯代父出征,砍杀敌人的头颅回来洗刷家庭的罪。督布斯出战了,他这一次必须砍敌首回部落立功赎罪,为他的家庭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但是,正当督布斯跳进敌人的窝点时,发现没有其他的敌人,只有一个日本女人,督布斯带着杀红了眼的杀气砍下一刀,却把刀砍进了女人旁边的一棵木柱里。在督布斯拔刀之时,女人宽大的日本衣服下露
出一个小女孩的脸,女孩眼含泪水并颤栗着,督布斯一下子想起自己的妹妹烧伤的痛楚。这时有人喊:“督布斯,你快砍了头走,敌人的援兵会很快到的。”督布斯挥刀砍倒木头房子的支架,并把房子推向山沟,然后挥刀割下日本女人的一绺头发,追赶队伍去了。回部落后,有人说听到督布斯进的木屋有女人声音,怎么就没砍下人头呢?督布斯说那人跳崖了,他只捡到头发,他拿出自己故意割的头发违心地为自己作证。后来妹妹问他缘由时,督布斯告诉妹妹:“因为我不想杀自己的妹妹。”他讲了一个其他的故事给妹妹听,不想让妹妹再问他砍日本人人头的事,聪明的妹妹了解了一切,打断他的话问:“她能不能算是我的妹妹?”督布斯回答:“不能,因为她们的神和我们的神不是住在同一个地方。”再后来,日本人杀害了布农族的抗日首领,占领了布农族地区。日本人常常集中部落族人,强行发日用品给族人。一次,督布斯也被押去领日本人的东西,有一个妇女拿着一捆棉被向他走来,弯腰并说了一长串日语,旁边懂日语的部落老人告诉他:“她的女儿已经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去读书,不久的将来她也要回去照顾她的女儿,这个棉被表示她的谢意。督布斯,你认识她?”原来这位给他棉被的日本妇女就是他欲杀而又放走的日本女人。
这是一个忧伤的故事,主人公督布斯的行动没有挽救自己家庭的荣誉,反救了敌人中间的无辜者——日本母女。督布斯个人也由此陷入一个悲剧,他无法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线,但他又无法不为自己辱没了祖先习俗的举动而感到羞愧和愤懑。这让一个极想成为英雄的布农男孩不得不负担一生的心理耻辱:个人为家庭奋斗的理想没有实现,集体的使命又象蒲公英般飘零飞荡,对一个男孩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但是,恰恰是这个沉重打击显示的悲剧意义揭示了布农族传统人文观念里关于善、恶的近乎真理性的认识:“生命是由善、恶组成的,但生命具有选择善、恶的权力”。男孩督布斯凭借自我经验和智慧选择了“善”的举动,彰显了原始习俗中强调正义及善良精神的本质存在。
如今,日本侵略者早已被打败,抗日战争胜利已60周年,但是原住民抗日文学的解读才开始。和平年代里,反映战争的文学创作和解读、反映战争的文学作品是对战争和侵略者是一种警示,一种警惕,对爱好和平的人们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再认同。
投稿方式:
电话:029-85236482 15389037508 13759906902
咨询QQ:1281376279
网址: http://www.xinqilunwen.com/
电子投稿:xinqilunwen@163.com 注明“所投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