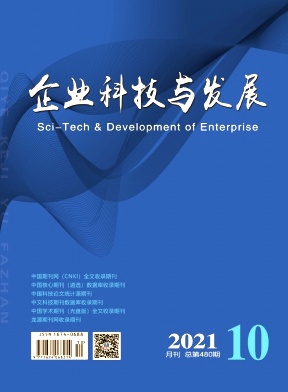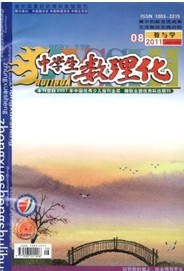浅析中西文学创作中的写景差异(一)
文学是人学,以体现人为最高意图。中西方文学创作在对这一准则到达默契的一起,并没有无视写景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意义,人与自然景象的实际联系在文学创作中遭到尊重。仅仅因为中西方在长时间前史发展过程中所构成的两大文化传统的差异,而使得在人与自然的联系中,人对自然景象的掌握、认知方法,必定贯穿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而构成不同的体系。其间,直接间接地影响作用于文学创作的审美意识及美学思维,差异尤为显着,对写景在中西方文学创作中的种种差异的意识掌握都由此而生。
首先,从审美意识上来剖析,“写景”在中西方文学创作中因审美意识的不同而在艺术态势上出现不同的走向。
在人对自然景象的审美活动中,咱们不难发现,中西方在审美意识上所体现的根本差异在于:西方普通总的倾向,往往是作为审美主体的人与作为审美客体的景处于相待状况,主体(人)对客体(景)进行赏识,因而人与景的两边事实上处于相互分立和坚持的联系中。中国普通总的倾向则与之有别:主体没入客体,客体融于主体,人与景的两边暂忘彼我,到达相互符合的一种调和默契境地。中国古典诗篇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等等佳句中描绘的都是这样一种境地,这种人与自然的调和之美正是中国艺术的精华地点。
这种审美意识的差异,取决于中西方美学思维的侧重点不同:中国向来是重体现、抒发、言志,而西方重再现、摹仿、写实。
正是因为这种审美意识和美学思维的根本差异,构成了中西方文学创作在写景方法上的显着差异,然后发生了艺术态势的内倾和外倾的两种走向的分野。大致说来,西方因尚“进步”,而在写景艺术上体现出一种“浮士德精神”,即多向外探究。这种显着的外倾态势招致了西方写景艺术上的侧重“描物——描绘(再现)外界的自然景象出现于人眼而被感觉到的客观“形象”。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对巴黎圣母院的大段大段准确详尽的描绘,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对战争场面的煞费苦心的雕琢等等,都是西方文学所拿手的写景方法。而中国因较“本分”而偏于内向,总是喜欢到心里去搜索情感的表达方法,故而体现出一种中国文学共同的“老庄精力”,在写景艺术上出现显着的内倾态势。它注重“体现”自我所感及所识,也就是情景交融、物我相渗、主客同一的景与人两边内涵生命律动的“气韵”。人与景在审美机制中构成了“双向同构”联系,自然景象取得了人物豪情的同化,因而也产生了情。这里人与景的双向同构的主导方面是人。一旦无人,情消逝了,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王国维所谓“全部景语皆情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剖析的。
首先,从审美意识上来剖析,“写景”在中西方文学创作中因审美意识的不同而在艺术态势上出现不同的走向。
在人对自然景象的审美活动中,咱们不难发现,中西方在审美意识上所体现的根本差异在于:西方普通总的倾向,往往是作为审美主体的人与作为审美客体的景处于相待状况,主体(人)对客体(景)进行赏识,因而人与景的两边事实上处于相互分立和坚持的联系中。中国普通总的倾向则与之有别:主体没入客体,客体融于主体,人与景的两边暂忘彼我,到达相互符合的一种调和默契境地。中国古典诗篇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等等佳句中描绘的都是这样一种境地,这种人与自然的调和之美正是中国艺术的精华地点。
这种审美意识的差异,取决于中西方美学思维的侧重点不同:中国向来是重体现、抒发、言志,而西方重再现、摹仿、写实。
正是因为这种审美意识和美学思维的根本差异,构成了中西方文学创作在写景方法上的显着差异,然后发生了艺术态势的内倾和外倾的两种走向的分野。大致说来,西方因尚“进步”,而在写景艺术上体现出一种“浮士德精神”,即多向外探究。这种显着的外倾态势招致了西方写景艺术上的侧重“描物——描绘(再现)外界的自然景象出现于人眼而被感觉到的客观“形象”。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对巴黎圣母院的大段大段准确详尽的描绘,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对战争场面的煞费苦心的雕琢等等,都是西方文学所拿手的写景方法。而中国因较“本分”而偏于内向,总是喜欢到心里去搜索情感的表达方法,故而体现出一种中国文学共同的“老庄精力”,在写景艺术上出现显着的内倾态势。它注重“体现”自我所感及所识,也就是情景交融、物我相渗、主客同一的景与人两边内涵生命律动的“气韵”。人与景在审美机制中构成了“双向同构”联系,自然景象取得了人物豪情的同化,因而也产生了情。这里人与景的双向同构的主导方面是人。一旦无人,情消逝了,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王国维所谓“全部景语皆情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剖析的。